原创 陈继芳 缙云县好溪文化研究中心
【村办公共食堂】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村叫“生产队”,乡叫“大队”,后来把村叫大队,乡叫公社。村民都是“社员”。1957年,生产队开始办“小食堂”,一队一个食堂,农户自家的灶台都挖掉了,锅拿去熔铁炼钢,几十户农户共用一个食堂的灶台。当时那灶台的户主是孔银田(孔瑞安的曾祖父),他家附近有一口水井,方便挑水煮饭。一个食堂管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只管煮饭,一个只管挑水劈柴。米和菜都由农户各自带去食堂,据说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除了管食堂的两人,其他人都参加生产队劳动,生产出的粮食全队统一分配。当时每人还有六十平方的“自留地”,种出的农作物,社员自由处理。
1958年设了学田村全村的“大食堂”,位于现在的盘山东路孔星水住宅至孔维神住宅一带,土名是叫“花屋里”,(原来的“花屋里”是“全个台门”——一种建筑样式——遭过火灾,重建之后不再是“全个台门”了,但还叫“花屋里”),统共九间楼房,楼下的房间,拆掉木板的墙壁相互连通了,两间安灶台,剩下几间放几张木方桌,一队一间,楼上仍然归村民居住用。村民白天一同劳动,粮食由村统一翻晒、入库、加工(那时没有农用机器,粮食加工全靠村里隔墙碓、下水碓两座水碓(一种水力驱动的舂米的工具),分别在现在羊山坞口桥头供销社路边平房和吕法德住宅处),村里统一按年龄每月发饭票,十八岁以上每人每天十四两(当时的一斤还是十六两),最少的只有二两。早饭基本是粥和玉米羹,因为粮食常常不够吃,粥和羹总是煮得很稀,不顶饱,勺子放进锅里时,会听到“咚”一下砸到底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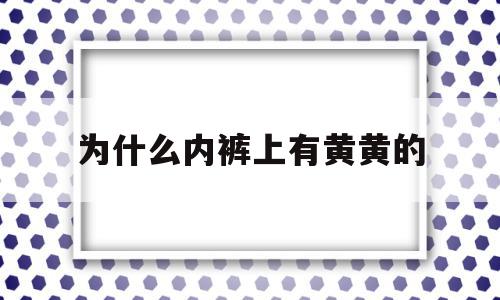
午饭吃的是蒸饭,有的用铁罐盛,有的用碗盘,有的用盃头,还有的干脆找一截比较粗的竹筒,削掉篾青,就能凑合,我也曾经做过,在竹筒一侧留一厘米左右的篾青,在那中间上下钻两个洞,再用铁丝把两个洞连起来成柄就能用了。用竹筒蒸的饭特香,现在还被一些农家乐当做特色保留着。饭票也常常不够用,许多人没到月底就吃完了,只能挨饿。我的母亲比较精明,每天的饭票都算好了,不多吃;又勤快,常常在空闲时候去采野菜,一般是苦菜和荠菜。采回家,装在风炉小锅里烧熟了撒上一点点盐(没有油),拌进食堂打来的稀粥、羹,就稠了,就能吃得饱一点。那时大家一起劳动,吃“大锅饭”,多干不多得,根本提不起村民们的劳动积极性,加上农作物品种不好,粮食亩产低,于是天天一天到晚都感觉饿,在学校上课的学生们每每到第三节课就在想吃饭了,根本没法集中精神学习。因为缺少粮食,大家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山笋、野草、野麻叶、柿树叶、长毛草、革命草、紫云英、红薯叶、土豆叶、玉米壳粉、花生壳磨的粉……为了填饱肚子什么都吃过了。有一种茎块像大葱的植物,又圆又白,但是有毒,要用清水浸过三十六次才可以吃,所以叫“三十六桶”,但是体质差的人吃多了还是会中毒,会水肿、腹泻;有两种土名叫“山鸡粮”和“百梗刺”的植物茎块,可以充饥,但是人吃了会便秘、便血,严重的还有肛裂。我那时的一个邻居,就是这些吃多了拉不出大便,只好脱下裤子让老婆用勺柄捅进去挖,疼得大叫,越叫越疼,越疼越叫,好似猪的嚎叫声,然而那个年代我们不仅吃不到猪肉,甚至很少见过猪跑。
那几年老人生病了都无法医治,都是面黄肌瘦、浮肿无力的样子,村里能分几斤麸皮、几个带鱼头都算是营养品了。
【②村办养猪场】
大队里专门办了养猪场。下宅口自然村的社员们,都住到学田村来了,他们下宅口的房屋都改建成了猪棚,养的猪宰杀了全村人分吃。名义上是有养猪场,可那时人都吃不饱,又哪有粮食给猪吃?所以这些大牲口们一年下来也长不了几斤肉,都是瘦骨嶙峋的,所以村民也吃不到多少荤腥。那个年代,谁能吃上一顿猪肉,就相当于现在在五星级饭店吃大餐了,可现在顿顿有肉、发育过度的年轻人们是想象不出这样的生活的。当时流行一句话:“猪肉加白米饭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从前苏联的“牛肉加土豆就是共产主义”套用过来的。
大队还专门成立了种菜组,组员大多是五十来岁的老农民,因为他们懂时令、通农活。孔祥灶就是种菜组的。原先中央台门溪边的一块大约九百平米的地块就是专供种菜组种菜的,其实也就种些南瓜、萝卜、青菜。有一回我母亲在溪边洗衣服,那田里有人在锄地,顺手把发现的小石块捡起来就往溪里扔,不偏不倚地砸在她的头上。所幸伤得不重。
【③背柴组】
还有背柴组。组员都是个子大力气好的人。背来的柴都堆放在大食堂门堂里。他们都贪小便宜,总是把搭柱带回家,后来背回来的柴越来越轻,带走的搭柱却越来越重,从七八公分粗直到十多公分粗,十多斤重,只要用力按一下搭柱整担柴都会被撬起来。有一次大食堂没柴火烧了,村干部听说背柴组的孔朝福带走了很多搭柱,都藏在自家楼上,就带着食堂的工作人员去他家要拿回搭柱来解决柴火的问题。朝福一听说村干部找上门来,脱得赤条条的站在楼梯口,村干部见了,怕沾了晦气,只好回来。
他朝福也算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汉子了。
【④半箩稗籽,一人自杀,一人坐牢】
有一回,因为缺粮,大队社员收稻子时把稗谷也收起来了,有半箩筐,好歹也可以磨粉吃。可后来的社员把谷子也倒在了这个筐里盖住了稗谷,这半箩稗籽就这样子“找不到”了。村里有名叫“小球”的女人——人如其名,个子不高——举报说这半箩稗籽是兰香偷的,因为兰香家就在那仓库隔壁。村干部就把兰香叫去审,小球也来当面对证。兰香没法证明清白,回家后就吃了一种叫“菜虫药”的有毒树叶子自杀了。这半箩稗籽多日后被找到了,小球因为诬告害死人被判了三年有期。孔德雨因在集体番薯地上捡了几块番薯回家,有人举报是偷的,村干部扬言要抓去斗,孔德雨害怕,竟也吃了菜虫药,死了。
有一回,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婆婆,打了稀饭放在食堂的桌子上,走开了一会回来看到稀饭里有黄黄的液体,但是她眼神不好,看不清是什么,旁边的人提醒她,食堂楼上有人住,那桌子上面正好放着便桶(没有抽水功能,就是一个木桶加个提把),恐怕是小便滴上去了,就别吃了吧。可老婆婆舍不得倒掉,还是吃了。
有一回,一个二十来岁、打着两条辫子、从方前来的姑娘,在学田村口路边的地里折了一根玉米茎吃(因为没结玉米包的玉米茎是甜的,可以当甘蔗吃,是上个世纪孩子们喜欢的“零食”,有些时候还能解渴),就被发现的村干部捆起来示众,那姑娘大概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被绑着嚎啕大哭,背上还插着没啃完的玉米茎。
我的一个邻居,平时就爱贪小便宜,擅长顺手牵羊。有次他在集体地里偷了几块红薯,正放在临时砌的小灶里煮着,村干部就找上门了。他当然矢口否认,其实村干部都闻到红薯味了,就故意说“真没偷过那就算了”,转身便走。他见村干部走了,马上关上门,掀起煮红薯的锅子的锅盖加了一点水,这时候躲在门外的村干部夺门而入,人赃并获,“铁证”如山,他只好认罪。
每次收获了玉米之后,会召集女社员晚上一起“揉玉米”(就是脱粒),有些人就会故意穿双雨鞋来,揉玉米时“不小心”“掉”几粒进去,可以带回家炒起来吃。也有的会穿条雨裙(不是现在的小姑娘们穿的那种长连衣裙),也可以夹带一些玉米粒。但是遇到认真的干部,这些小手段就行不通了。
因为饿,老实人也会起歪心思。有时候玉米收获时正值冷天,不能及时晒干,就会堆在李国南大门堂的屋里(当年还是公用的屋子),那屋里靠大门堂这边的地皮有条缝,小孩子的手刚好能伸进去,因为玉米是一直堆到那边的墙板的,会有一些玉米掉进去,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小孩就一起去捡玉米。记忆中,捡到的几小把玉米都放进了一个小圆铁盒里,架在火炉里转烤,烤出来的味道似乎比现在的任何零食都香。打豆场的豆子、晒谷场的玉米粒也成了我们的“烧小食”。
我们去小学上学都要路过现在的学田街一带,那里有一片麦田,还有一棵枫树。春夏之交,麦子尚未熟黄,我们早上提个火炉去上学,四下无人时就会摘走几个大的麦穗。到了田坎下,把炉子的炭火吹红热了,把麦穗整个塞进去,一边吹火一边翻着麦穗,听到“噼啪”几声,就是可以吃了。我们那代人,人人都有自己的“求生之道”,胃口特好。
过了两年,粮食产量越来越少,每人的口粮已经不能按最初定下的分量分发了,村子的大食堂只得解散,改为两个生产队的小食堂,我所在的六队和五队共用一个食堂,用新屋孔志新的三间平房(后来是国良的住所)改的,由李廷扬和孔德喜负责。李廷扬是六队的,管财物,孔德喜是五队的,管烧饭。名为食堂,其实只是个空架子,因为根本没粮食可供了,一天只能供给一餐,其他都要社员自己解决。农户都各自立起小方灶、大风炉,正应了那句老话“倒灶泥风炉”。
有一年春节,食堂破天荒地提供包子给社员,虽然只是用掺了细糠的面粉加上一点咸菜豆腐凑合包起来的,但在当时已经很难得了,因为这一顿包子用掉了好几天份的面粉。
【⑤大协作】
何为“大协作”?就是整个大盘镇—大盘公社范围内,村与村之间不分你我,哪个村有什么需要,其他村都要无条件提供帮助,就是后来说的“平调”。一是生产大协作,村民要到别的村干活,但是因为对自己没好处,肯定都是出工不出力。领导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像现在幼儿园里给小孩子们脑门上贴小红花、小星星一样,在村民背上插小旗子,由干部监督,谁卖力,就插一面小红旗,谁偷懒,就插一面小白旗。有一次我们队里一名姓蒋的农民在掏山(我们这的土话,开荒)时突然流鼻血了,就停下来,结果干部不管不顾地给他背上插上一面小白旗,他干脆一屁股坐地上不干了,干部知道了原因,也拿他没办法了。
1957年至1960年这几年,农村的水库大部分是在这时候建成的,没有重型工程机械,全都是人力一锄头一锄头,一挑子一挑子建起来的。那个时候,不仅劳动力要“平调”,土地也要“平调”。比如,水竹湖的水库,地基是用的殿下村的田,由学田村出人建的;石上塘坞的水库,是小盘村在学田六队的地上建的;甲坞岭头的塘,地也是学田六队的,但塘是甲坞人挖的……这样的事还有很多。
【⑥大办钢铁】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前苏联撤走了在中国支援建设的所有专家,我国的工业发展受到严重挫折。毛主席为此发出了“自力更生”的号召,提出了“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一构想据说是毛主席依据法国的“巴黎公社”提出的,要把中国农村乡一级的基层政府组织为公社,直到1983年才改为乡政府。
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就是各方面都要有飞跃性的发展,首先就是粮食生产“放卫星”,各地都有小麦亩产超五千斤、棉花亩产五千斤、水稻亩产超万斤、甘薯亩产五十万斤的虚假新闻,其实都是把许多块田地的作物移到一块地里,收成全算作这一块地的,我们村也搞过:种田的时候提倡二寸乘五寸的密植,把几块田的未成熟的稻子移植到一块田里,结果是原本种着的和后来移植的都成熟不了,造成了大减产。
那年提出钢铁要年产三千万吨。毛主席指出:“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于是乎全国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热潮。大盘的炼铁场在学田村的大门堂,在这里以村为单位各自建起了炼铁高炉,高炉是土法建的,高三米多,直径约一米半,肚子大两头小,砖块砌成,外面糊上泥浆。
村里再分几个组,由二十多岁身强力壮的村民兵带队,轮流在炼铁场工作,进炭,进铁末,出铁。还专门组成了一个组去烧炼铁用的炭,吃住都在离村子二十几里路的长短坞、水竹等木材多的山上,我们队的万连阿公就在这个组。据他们说,土法烧炭都是在地上挖个坑,把木柴放进去,点火,等烧得差不多了就用土把坑封上,因为要准确把握火候,不能让木柴烧成灰,所以烧炭组的组员都是比较老成的社员。烧炭的工作虽累人,但也有好处:一是人自由了点,干部管不着;二是烧炭剩下的灰可以做肥料在山上自由种菜,能填饱肚子;三是可以在早晚的空闲时间用木材做些小家具。万连阿公就做了一些。把一段空心木材刨、削、凿成管状,再做上一个底,做一个小提把,就是一个小木桶,可以装饭盛菜。
还有挑炭组,都是力气好的人,把炭从二十多里外的山上挑回村里。
还有洗砂组,每组四五人,老人妇女也可以。工作是用土法淘洗溪里挖上来的沙土,淘洗出铁砂来倒进高炉炼铁。具体做法是,首先取一块门板,两边钉上一尺宽的木板做成一个槽,一头用东西垫起来,上端有一条泥石堆成的小坝,让水流进槽里,几个人把其他人挖来的沙挑来倒在木槽内,另有一个人用扫帚搅拌,沙随水流走,留下一点点铁砂。用这种“小水淘沙”能得到的铁砂很少,效率很低。大门堂炼铁不分昼夜,一整天都是火光冲天的。二个民兵连比较有名气,分别是林丰村的和市口村的,村名写在那时候的“公告栏”上——就是在大房后墙上用石灰粉白了墙,用黑色柱形记录各村政绩。林丰村的民兵连长蔡加兴,因为炼铁时出铁量经常是第一,就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编了《加兴炉子有十好》来唱;市口村民兵连则是用独特的方法出铁,别人都是让铁水自己慢慢流出来,他们却直接让几个民兵用撬棍、杠子把炼铁炉撬起来,流铁水很快,还出过一次事故,伤到了人。
后来为了技术革新,还在现在晓弟住宅的位置建了一个高十几米、直径二米多的高炉,可惜不知为什么从没使用过,后来倒成了小孩们“躲猫猫”的好去处。那几年农户家里的铁锅、犁头等等带铁的都拿去熔了,美其名曰砸锅卖铁支援国家大办钢铁。
大办钢铁结束后,建炼铁炉的砖、泥还有铁碴子都留在了大门堂,大门堂的地基都被垫高了四五十公分。
【⑦打一堂葛衣,死了三个人】
一九六二年的冬天,我们遇到了饥荒,还有力气的人们都上山去挖葛衣了,可以加工出淀粉充饥。
孔天云与我同龄,个子不高但是壮实,同龄人给他起的外号是“呆头金杯”。我和他是好朋友,还记得不少他的事。十三岁时他的力气就不小了,已经跟着父亲孔德水劳动,上山挖葛衣时他自然也是要去的。挖到的葛衣拿到水碓打碎再过滤成粉。谁要用水碓都要跟管理人事先预约,按定好的次序排队使用。出事那天本不该是天云家用水碓的,只是他父亲向那家人求情,说家里已经没了粮食,请他帮帮忙,让他家先打,那人心软就答应了。那里有两台碓头,一个是供销社的付(傅)立富在捣火药,天云他爸和天云就用另一台打葛衣。出事故的原因全在付立富。按理加工火药的时候应该用木锨搅拌,可付立富却在用铁锹搅拌。铁锹与石臼摩擦出的火花引爆了火药,三人都被炸得不治身亡。也是造化弄人,因为半箩稗谷含冤自杀的兰香就是天云的母亲,他们一家人都不得善终。
2、本站永久网址:https://www.yuanmacun.com
3、本网站的文章部分内容可能来源于网络,仅供大家学习与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站长进行删除处理。
4、本站一切资源不代表本站立场,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5、本站一律禁止以任何方式发布或转载任何违法的相关信息,访客发现请向站长举报
6、本站资源大多存储在云盘,如发现链接失效,请联系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
源码村资源网 » 为什么内裤上有黄黄的(为什么内裤上有黄黄的液体)

1 评论